十年城匣
我撑船穿过那条溪,只身前去看一场花事。开了,又谢了。
鱼肚泛白,溪边浣衣,昔日的吴越之地遍地麻衣楚荆。吴侬软语入耳,巧笑倩兮入目。
水是水草的城,雨是烟雨的人。城中人,人入城。雨在水中交融,人在城中往来,曾有些许繁华。
而墨是一种神奇的苦水,它染黑了城中的烟雨,漂亮了诗人多愁善感的心情。彩色逐渐变得陆离光怪。我听到它用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换来的小城的篇章。
——“子规啼
叶鸣廊
云连哀草浣溪沙
花惊寒食日
柳认清明时
脉脉蒹葭缘溪庭
望断路
月迷津渡
游子归来
回首斜阳暮。”
而我,以一颗游子的心映证了这一诗篇。
绿色疯长的季节,我回到了这座生养我十多年的故城,回来看一场花开的喜事,叶长的生气。古镇,旧路,繁花,江月,春水,这些都与我记忆中的残影渐渐重合,恣意蔓延着昔日乐章里跳跃的音符。
我的故城的匣子被打开,故事散落一地。
十年前,我还是个未长成的懵懂的孩童,还是一个光着脚丫子疯跑的年代。而我,被大人们认为是性格怪癖、乖张。在路上走的时候,尘埃绕着空气奔跑,我就小心翼翼地淌进浅浅的布着水草的水底,水小小的冲击力轻覆着我脚底的柔软,水面上绽开了辛夷的芬芳。
青石板小道上的角落里肆意地生长着绿色的苔藓,湿漉着空气,穿过这条路另一条街的拐弯处,在同样的角落我看到了衣衫褴褛的灰暗的他们——老人和他的小女孩。我最先注意到的是那个小女孩脚上的鞋子,他脚上套着的是前几天妈妈扔掉了的我穿坏了的小皮鞋,而她,也是个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小孩。老人穿的衣服很少且破烂,头发稀疏到可数,脸上布集着岁月的河流流过的沟壑,而河流底部残留的沙成了他脸上的胡渣。
年幼的我把他们当成了乞丐,内心酸楚双脚踌躇,最后我小跑着过去把妈妈给我的钱扔到他们面前,然后踩在潮湿的苔藓上小跑着回家了。
那次我挨了打,我用哭得红肿了的双眼看到窗外的桃花开了。
七年前,我又看到了小绵爷爷他们,是的,我当初误以为的乞丐。我看到他们在学校门口摆了小摊卖棉花糖。地上一朵一朵散着甜味的花,天上一朵一朵变幻的云。
于是每天放学后,我总是去小绵爷爷那买棉花糖,所以我叫女孩小棉,老人是小绵爷爷。我带着书本给小棉看,因为小绵她还没办法上学,然后我又从家里搬来小板凳坐在爷爷的旁边。我安静地听着小棉爷爷绕棉花糖的声音,和小绵轻声读书的声音,无论天晴或是天阴,我都会在他们身边耗一会儿。
小绵爷爷说,他们是因为家乡闹灾荒才流落到这边,他们贫穷但也要自力更生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闪着奕奕的亮光,一只手递过来一支糖,说:“喏,爷爷请你吃。”我接过糖放在嘴里砸巴,池塘里荷花的清香熏得我眯了眼睛,尽情地拮香,嘴巴张咧着,不知是因为荷香还是因为小绵爷爷。
夏日的时光总是飞速的,就像乱石间生长的杂草,昨日才冒了个尖,今日就枯黄了脑袋。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些老弄堂、青石板路和化不开的棉花糖里逝去。
三年前,我离开了小城。我对小绵爷爷说,我会回来的,然后我带着行李和身影踏上了异乡的路。
我走的时候,我看到河里的水草变得更加茂密,紧紧地挨成墨影,天刚下过雨,徒添秋意,莲花未落尽,我偷偷拈了几分馀香,双眼又眯成一条缝,道是“芳草不迷行客路,垂杨只碍离人目。”
而今,我脚下所站着的斑驳了的旧砖路上的青苔藓又泛了绿,我需要很小心很小心地走过这一带小路,再来到从前我常放小板凳的那个地方。那里空无一人,我突兀地站在那里,找不到我的小绵和小绵爷爷。
远处的渔船点上了灯,连灯都透着新生的气息,它泛着黄光挂在那里摇晃。然后它又伴随着船摇晃着穿过桥底下。船驶过的河面泛起迤逦的波痕。
日阑风静,我立在江边倚歌听江声。江南咸湿温热的气息在江面上泛起光环,晕成红白交接的光,那里是太阳落下的江平线。没有了光亮,也就暮色降临了。
十年前的记忆停止了在角落生长,我将它打开,古城是一座匣,回到匣中,回忆也就随之而至了。依旧是软语入耳,麻衣楚荆,墨色点尘。
而刺桐花落尽,江南怕流莺乳燕,乳燕会归,游子亦也会归。只是当游子归来,她再也找不到十年前初遇的她所最想念的人们。
十年城匣,打开了便不可收拾。
本文地址:十年城匣https://www.chaozuowen.net/a/6598.html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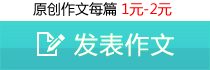


猜你喜欢: